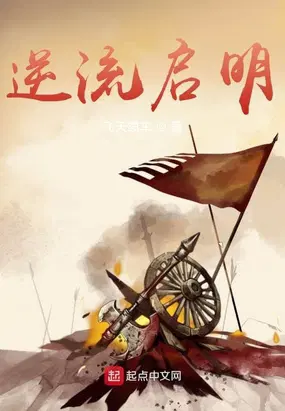第1064章征税 库页岛很大,资源也很多。 但缺点也很明显,地太偏。 恐怕只有等到工业时代才能进行开发了。 如今的库页岛最大的资源,莫过于许多大马哈鱼和野兽了,石油和黄金只是深埋地底。 若是论资源,哪有南洋来的多,来的简单? 朱谊汐仍旧分封藩国了。 好地方只有占了,并且守住了,才能给未来做打算。 库页岛那么大,黑龙江总督府连内陆都没开发十分之一,哪里顾及的上库页岛这样的苦寒之地。 将半个库页岛作为给越国的补偿,让其助力开发,最好是大量移民,才算是合算。 越王很高兴,父皇对我还是挺在意的。 朱谊汐又问起了越国的问题。 越王讲述了与日本交易之事,尤其是涉及到战马,更是小心。 对此,皇帝倒是浑不在意:“日本幕府统治其地,名为国王,实不过是共主吧,其组建骑兵,最要紧的就是镇压藩国、乱民罢了,不虞其威胁。” 就像是日后列强卖给满清武器,根本就不怕满清雄起反杀。 日本两三千万人,看上去很庞大,但却被细分为三四百个小藩国,可谓是松散的厉害。 德川幕府这架马车,从第四代将军德川纲吉开始,就饱受财政不足的困扰。 因为幕府的财政,基本依靠德川家的四百万石天领,以及矿山支持。 但金银外流,矿山枯竭,导致财政收入不断缩减,而武士阶级数量不断滋生,以至于开销越来越大。 而奇葩的是,江户几乎每隔几年就发大火,修缮江户城就是德川幕府中后期最重要的支出了。 其就如明朝一样,被财政问题束手束脚,成了跛脚巨人。 可以说,只要维持如今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令,一两百年内越国都会没事。 “汝在越国,上为黑龙江,左为朝鲜,南为日本,左右逢源自然可行,但须知农业才是根本。” 朱谊汐语重心长道:“如果耕地不够,那么就建立牧场,畜养牛羊,无粮不稳呐!” “儿子知道。”越王点点头。 “我听说你越国苦寒,伐木怒暖能击几时?” 朱谊汐随口道:“多找一些煤矿,取暖问题解决了,到时候移民还怕没有吗?” “况且,你二哥都能寻摸到金矿,铜矿,你就找不到?到时候自给自足,还怕个甚?” “儿臣明白了。”越王眼前一亮。 他倒是一直被沿海平原给困住了,对山地畏之如虎,倒是没有想到找矿。 有了金矿,做生意才赚几个钱?还担惊受怕的。 旋即越王说起了乏人之事。 这属于老调重弹,朱谊汐没好气道:“哪个藩国不缺人?你二哥都快急上火了,这事得慢慢来。” “我禁锢过你们迁移百姓吗?只要肯分田分地,天下的贫民有的是,就看你有没有胆量吃下了。” 越王低头不语。 一户移民,近一年内都需要朝廷供养,吃食衣物,年均十块银圆。 迁移一万户就是十万块。 其余的房屋成本,土地开垦成本,更是极大。 若是分配荒地,那还得多养一年。 就这还不一定有人愿意来,毕竟破家值万贯,背井离乡很难被人接受。 只有受了灾荒,一无所有的贫民才愿意。 难哦! …… 秋收冬藏,在收获的季节,不仅是百姓们忙碌,地方衙门也同样繁忙。 北方的冬小麦是九月栽种,来年五月底收获,历时长达八个月,是黄河以北,长城以南的主要农作物。 河南,卫辉府,淇县,古之朝歌所在。 河南之地在崇祯末年,元气保存最多的乃是位于黄河以北的三府:卫辉、怀庆,彰德。 也是如此,绍武年一来,三府就迅速恢复了生产,然后陆续向河南腹地迁徙。 也是如此,再加上湖北的移民,河南九府(一直隶州变为府)迅速地恢复了元气。 绍武初年,阖省不过三百万,如今已至九百万,可谓是极其夸张。 在大明全国各省中排第四,排第一的为山东,一千二百万人,江苏一千一百万,以及江西的一千万。 在不征收丁税的情况下,百姓们也不隐瞒了,纷纷上报真实数字,清朝的人口暴增,也是如此。 如果朝廷不再征收田税,那么可以预料,田亩数起码能翻个倍。 “老爷,今个还下乡?” 女人一身襦裙,戴着银钗,正弯着腰在鞋柜中点数着,臀部勾勒出一道弧线,诱人的很。 张竹却没兴致,他缓缓地穿着皂服,随口道:“没错。” “麦子不是六月收了一次了吗?” 女人放下步靴,找来一双木底的猪皮靴来,很是耐脏。 “玉米,或者高粱。” 张竹知道妻子是宅中女子,随口道:“冬小麦九月播种,五月收,农夫还得再种一茬玉米,这个产量高些。” “不得闲咯!” 叹了口气,他一身皂服,红黑相间,倒是显得很是威风。 与其他的衙役不同,他胸前的白色补子上,写了个大大的税字。 他就是淇县的税吏。 走出三进的宅子,他坐上马车,施施然地抵达了通判衙门,挎着刀就走了进去。 路上,许多同样皂服的小吏,则恭敬行礼,只是因为他们胸口没有税字,只是淇县数百名的白役之一。 通判衙门略小于县衙,同样也是前衙后堂模式,占地约三十来亩,房屋五十间。 偌大的衙门并非通判专属,实际上分为了四部分。 最大的是案堂,顾名思义就是审案的,包括通判老爷的卧房。 其次是推官,被誉为二老爷,专门负责案情审判,只要不是命案,就由他审判。 第三,自然是牢狱,其占地十余亩。 其中,看押重罪犯的“监”,拘禁轻罪犯人的“羁铺”,羁押欠债罚赎人质和人证的“差馆”等,拥有层次分明的三级牢狱体系。 最后,则是商税局。 商税局由之前的县衙税课局改名而成,专门负责征收商贾、侩屠、杂市捐税及买卖田宅税契,以及如今的农税。 换句话说,抢了县衙户房的权力,掌管本县所有的赋税。 而商税局则是由通判管理。 审案,看押,征税,通判的职责不小。 待张竹抵达衙门时,商税局的大院中,已经聚集了近六十号人。 而像他这样正经的吏员,只有五个,白役是其就九倍,在县衙中仅次于三班捕快。 正吏是有编制,有朝廷发的钱粮,而白役则是吃县衙饭,一旦某年县衙没钱了,就会拖欠,而且随时会裁撤。 税吏与普通的衙役最大的区别,在于他们可以挎刀,甚至衙门中常备马骡,巨大极大的威慑性和机动性。 有时候碰到刁民,县衙还不得不支使税吏。 商税局的司吏穿着八品的绿袍,头戴乌纱帽,挺着大肚子,施施然而来。 他也不啰嗦,在台阶上的椅子坐下,眯着眼睛道: “咱们忙的时候到了,规矩你们都懂,宁可多收,也莫要漏收,多收了顶多乌纱帽不保,漏收了就拿你们的家底来补,全家流放——” 底下一群税吏低头不语,面色平静。 农税和商税统一之后,赋税的征收不再由地方掌控,商税局虽然由通判监察,但实际上却受到了财部的直接领导。 每一任司吏,虽然财部无法任选,但却能罢黜重任。 这种双重管辖,让商税司戴上了紧箍咒。 像前明,以及其他历朝历代那样,随意征收杂税,新开杂税填补用度的做法,根本就行不通。 新明主打的就是一个控制。 “好了,全县刚好十个乡,一人两个,七天内必须完税,十月底要运至府城,可不能耽搁了。” 司吏随即分配起来名额来。 各乡有富有穷,普通情况下都是一富一穷,如果跟司吏关系不好,那就是两穷,关系好则是两富。 富者在平原,穷者在山地。 显而易见,张竹不好不坏,得了一穷一富,赵家镇,左后堡。 马厩中,他领了一头骡子,两匹驴来,领着十名白役出了城。 只是张竹一人骑骡,余下的两头驴空荡而行。 一行人浩浩荡荡,惹得路人 瞩目,不敢多言语。 “去赵家庄。”白役问询时,张竹随口道。 赵家庄处于官道旁,交通便利,平原众多,可为富庶,而左后堡则是卫所该制而来,地处要地,但却穷了些。 一行人抵达镇中时,乡三老们早就在路边迎接。 寒暄片刻后,就酒楼伺候。 酒足饭饱,还不待众人反应,乡里就塞了一些土特产入众白役腰间。 不多不少,十块银圆。 而到了张竹这,则是两张百块银圆的银票。 “这是天下钱庄的票子,您随时可以兑现。” 捏着银票,张竹不置可否,他眯着眼睛:“这可不符合规矩!” 往年都是一百银圆,如今翻到了一倍,这可让人惊诧。 他就这样直接看着这位乡长,毫无顾忌礼节。 一旁的乡老和乡警,则想要言语,却被乡长阻止。 他披着一件缎袍,方脸上依旧是笑意: “村里近些年多种了玉米,多在那山岭上,这不是想让公差们少跑些路……” 对此,张竹则轻笑起来:“据我所知,尔乡有地三万七千亩,水田近三千亩,旱地三万亩,山地三四千亩。” “去年约万亩,如今种玉米的多少亩?” “一万两千亩。”乡长一口道。 “休以为我不知道,你们乡多数都种了玉米,起码有七成,那就是两万三千亩!” 说着,他腾一下就站起:“我河南为中省,亩征二分,即二十文,两万三千亩就是……” “二二得四,二三得六,那便是四十六万文,即四百六十块银圆。” “我还算少了,只得七成,若是九成,那可不得了,六七百块钱呢!” 这还不包括未计黄册的土地。 这些年来,大户人家有余力开垦,小户也咬着牙用着积蓄开垦,最少瞒报了六七千亩地。 如果都算是,少征了千块银圆。 瞒报属于正常,谁也不想多征皇粮。 同样,朝廷也没用余力找到被瞒报的土地。 让张竹这十来人跟全乡人斗,还得摸底寻地,这比上天还难。 一个不小心还非常容易遭受野兽袭击,有生命危险。 “那您说算多少?” 乡长轻声问道。 “两百块不够,得三百块,另外,数量上得报到两万亩。” 张竹面色平静道:“大老爷(知县)要政绩,我们二老爷(通判)也是要政绩的。” 这割肉,让三老疼的不行。 乡长咬着牙道:“只能是一万五千亩。” 多让了三千亩,难受。 “行!” 张竹也识分寸,笑着应下。 见三老脸色难看,他继续道:“这钱虽到我手,但却不能尽数落入口袋,上头有司吏,再之上有通判老爷,我能落个三瓜两枣就不错了。” “这钱虽入我手,但却是在办你们的事啊!” 这话让三老们脸色舒展了一些。 至于商税,则是镇上的商贾之流,三老代收,也是三老们重要的钱财来源。 数十间商铺酒楼,以及菜铺、肉庄,还有分布在各村的草市,赶集。 其按照往日规矩,缴纳了七、八、九三个月的商税,共计一百五十块银圆。 这个张竹看不出来其商如何,只能循旧例,不再增减。 言罢,这场宴席才结束。 随即,一万五千亩地赋税,即三百块银圆就征齐了。 白役们提着鸡蛋或者鸡鸭,而张竹的两头驴,则背着大量的土特产,可谓丰收。 白役月不过半块银,半石粮,勉强温饱,这些外快才是他们滋润的根本。 乡里甚至要出人,帮忙将钱转运入县里。 三老们松了口气,随即招待二十五个村长: “老夫尽了力,税司不下乡查那隐田事,不过今次收了近五百块,你们每个村摊下二十块。” 听到五百这个数字,村长们立马就闹腾起来。 “往年不是三百吗?怎么多了两百?” 乡老是本地人,靠的就是各村的推举,他满脸为难。 乡长则不言语,只有乡警出面:“这不是种玉米的多了吗?人家又不是瞎子,还不得多收?” “各村按九成地来收。” 村长们这才罢了,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钱来。 然后则又是田税。 相较于税吏,三老们则宽松多了,允许各村在月底前送来,维护亲友乡土之情,村长们脸色才算是舒缓了一些。 村长回到村中,则道:“全村都要上税,隐田就交一半就成……” 百姓们乐于交一半税来保护隐田,改善生活,多积蓄而度荒年,以及其他灾病。 而这隐田,又是村、乡、县瓜分的利益。 受固于财政压力,皇权无法下乡,不得不妥协。 反而是商税,坐税的商铺固定,关税则有关隘,根本就逃不了。 ps:许多人说农税少,但两分,二十文真不少,冷知识,逼反百姓的三饷,加一起只有一分两厘,辽饷一开始只有三厘半。 清初合并三饷,亩征一分至三分,就这样也有六七千两。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