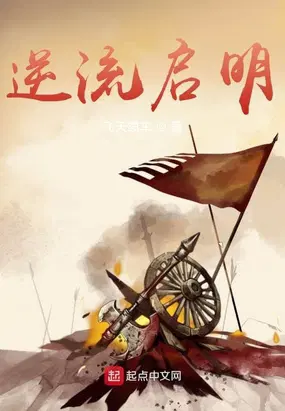哪壶不开提哪壶—— 这是在场众人的心思。 何腾蛟到底有些城府,脸色微变,旋即又恢复过来。 贵州文武互相看看,憋着笑意。 一旁的左良玉父子则脸色涨红,显然已经提到了他们的痛处。 “四川的归四川,与云南不一样。” 何腾蛟打了个哈哈,勉强兜转过去,瞧着沐天波还要再问,他才道: “如今贵州已聚集三万兵马,再征一些土司兵马,等粮草到位,就可出发了。” “国公,不知西贼兵马有多少?” 作为宁南侯,左良玉扯着嗓子,一副粗人的模样,在何腾蛟的示意下提问。 “这个,大概三五万,或者十来万吧。” 面对这问题,沐天波有些尴尬地说道。 众人眼皮直跳,对于这位不靠谱的国公爷,实在是无语。 敌人多少都不知道,这还怎么打,黔国公是怎么当的? “不过,总督,你们三万人着实不行,肯定打不过的。” 沐天波见到众人失望的表情,不由得补充道: “只要朝廷天兵入滇,地方土司自然箪食壶浆,起兵相迎,到时候破西贼,如探囊取物。” 左良玉隐晦地朝何腾蛟摇了摇头。 何腾蛟这才草草结束这场尴尬的欢迎,并且特地让人安置这沐府一家,绝不可怠慢。 国公的体面还是要有的,更关键是,沐府乃是破西贼的重要一环。 待只剩下何腾蛟与左良玉二人时,左良玉不由道: “督宪,这场仗不好打呀!” “我也知道。” 何腾蛟端起茶杯,细细品尝舌尖上的苦涩,其恰如他的心情一般。 原本以为,带着总督湖广、贵州、云南等省的头衔,平定西贼指日可待,势如破竹。 但谁知,在贵州就被卡住了。 无他,兵力不足,钱粮不足,心气不足。 兵力不足,乃是之前平定奢安之乱,导致贵州兵力大减,人口本就不富裕,如今应该是雪上加霜。 而钱粮不足,则心气不足。 但贵州这样的贫瘠之地,衙门养活自己都困难,更遑论支持朝廷出兵了。 当然,归根结底,还是钱粮不足。 贵州的蛮人不少,乃是上好的兵源,只要钱粮充足,自然能够招募不少人当兵。 “弟兄那边粮食都不够吃了。” 左良玉沉声道:“军中只剩下半月的粮食,再这样下去,什么军纪也没有,都只能去抢了。” “绝对不行!” 何腾蛟果断的说道。 且不说贵州是他的家乡,日后指不定被撬祖坟,就说如今贵州的局势,就容不得这等场面。 贵州与湖广,江西等地不同,这里土司众多,蛮人无数,一旦起了纠纷,脆弱的平衡被打断,怕不是没平乱贵州自己就乱了。 “还是得从长计议!” 何腾蛟纠结道。 左良玉无语了。 他对于这些文人的纠结实在搞不懂。 军队又不同于刁民,你要是不喂饱他们的肚子,人家真的会造反,到了这个地步更不堪设想。 “这样!” 何腾蛟咬着牙,说道:“暂且找几个不听话的土司清剿一番,再撑一段时间,我上书朝廷,让湖广、岭南弄些钱粮过来。” “这般再好不过。” 左良玉咧着嘴,笑了起来。 一旦独立领兵,他的机会不就来了吗? …… 南京。 弘光皇帝依旧放权,马士英与阮大诚团结一致,共同对付东林党。 而东林党则一直进行软对抗。 不过,仇怨越积越深的两方,此时却不得不聚集一起,探讨云南的事宜。 皇帝身体不适,马士英主持会议。 一个眼神,阮大诚作为并不侍郎,直接开口道: “何腾蛟传来书信,说黔国公逃出云南来到贵州,一身狼狈的求援……” 这份求援上书,到了通政司之后,几乎所有的高层官员都知晓了具体情况,但初一听,众人仍觉得离谱。 “黔国公明言,西贼养精蓄锐多日,聚兵十万偷袭昆明后,又裹挟着那些心怀不轨的土司,如今兵马超过二十万……” “云南十数府,目前仅存楚雄、大理等寥寥数府,可以说七成地界,都被西贼占据。” 说到这,阮大诚停滞了一下,才道: “而且,据黔国公所言,此次西贼并没有向往常一样屠城,裹挟百姓,反而安心治理起来——” “不好!” 此话一出,众人脸色齐变。 流寇不可怕,可怕的是坐匪。 云南的那些土司唯利是图,又畏威不畏德,一旦被西贼收服,就会酿成不可预知的后果。 所有人都承担不起再失陷一省的责任。 当然,北方沦陷,那是崇祯朝的事,与我们弘光朝无关。 “必须清剿,刻不容缓!” 钱谦益这时明白了其严重性,挺身而出,赢得了众人一片赞赏: “不过,何腾蛟要钱粮,江西肯定运不去,只能朝湖广,岭南想办法了,而湖广是最便捷的……” 说着,他的目光又看向了胸有成竹的马士英。 这下,轮到马士英骂娘了。 作为内阁首辅,也只有他有这个权利向豫王伸手了,其他人不够格。 宛如地方霸主的豫王,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?惹毛了,一旦来个勤王,那就闹大了。 而要是被顶,损失的是他这个首辅的威望。 不过,马士英这个首辅不是白当的,他自有两把刷子: “就下令给湖广布政司,让他们酌情支持一二,主要还是得靠广东。” 听到这,众人瞬间眼睛一亮。 如今湖广布政司名存实亡,所谓的政令最后只由豫王接收,给布政司而不是豫王,也造成了缓冲余地。 里外都照顾到了。 小小的刁难之后,东林党也只能妥协,不得不支持让广东来支持钱粮。 马士英松了口气,这是最近以来拉扯磨蹭中,最快的一次的。 回到宅中,已然是黄昏,又拉扯了大半天,钱谦益施施然地换上了常服。 娇妻柳如是伺候着,揉捏着肩膀,轻声道:“你那个学生已然等待了多时了。” “哪个学生?” 钱谦益一楞。 “就是那个满口怪腔,官话带着口音的学生,福建来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