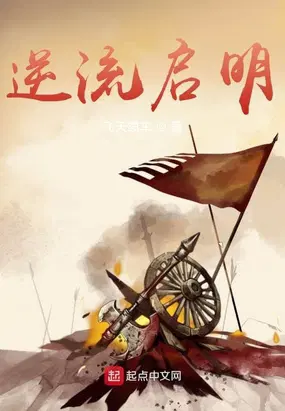灰蒙蒙的天空,仿佛一道垂下的帷幕,低沉地压制着草原上的一切。 “去,去——”朝鲁骑在马上,看着压抑的天空,忙不迭地驱赶起牛羊来。 几只猎犬也识趣地叫唤起来,跳跃着,省却了他不少的力气。 不一会儿工夫,一百多只羊就被赶回了羊圈。 他又不得闲,将拴在木桩上的两头牛解开,远离那仅余下草根的地面。 至于马儿,早就聪明地回到了马厩,窝在栏子中,躺在干草上迷瞪着。 朝鲁嘿嘿一笑,骑着马,牵着两匹马,带着木桶,去往了两里外。 这里有一口井,用石头遮盖的严实,砌上了砖石,辘轳上的麻绳已经发了毛,显然是用了不少。 这是朝廷的政策,也是为了促使牧民们定居,方便查验。 毕竟在草原上,无论干什么都离不开水。 除了河流外,井水的存在就会让牧民们不自觉地聚集起来,无法逃离朝廷的掌控。 牧民们也颇为欢喜,乐意这件事。 以往在草原上遇到干旱,河流枯竭,牛羊只能被渴死,而如今水井的存在,不知救活多少人。 朝鲁也是喜欢。 他总觉得人和牛羊同饮水河水很不干净,也很恶心,谁也不知道在上游会不会有尸体,或者粪便入内。 几年前他在千户社学那里听过半年的课,知道什么叫大明,什么皇帝,以及一些千户区外的事。 而不是像自己的父母那样,两眼一抹黑,啥也不知道。 “还是这水干净!” 瞅着井底的碎石,以及用砖头砌成的井壁,他松了口气。 他终于赶在井水浑浊之前到了。 木桶被捞起,然后又甩下去,提起来了。 足足装了四桶,每匹马背放置两桶,然后脚步迅速地回家。 果然,不到一会儿功夫,天空中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。 “果真是要下雨!” 他忙将一桶水倒在了马圈,余下的三桶则倒在大水缸,才满了七成。 这大水缸是他从市集上买来的,足有半人高,花了五毫钱才买到手,稀罕的很。 用碗舀起水入铁锅,然后吊在了火堆上。 他捡起干草,然后用镰刀刮了几下,引燃后放在火堆上,又架了两块木头。 似乎又不放心,他又放了两块煤炭。 “朝鲁!”这时候,从卧室里走出了女人的声音:“你在做甚?” “额吉,我在烧水呢,外面下了雨,怕是待会就得下雪了。” “哦!”额吉的声音平缓:“快黑了,你待会趁着火势煮饭吧!” “哦!” 作为家中长子,年不过十八的他并没有资格读书,家里也支撑不起。 二弟则去了喇嘛庙,送了十块银圆后成了小喇嘛,伺候在佛祖身边。 三弟则送到了千户所,给千户放羊,或者说一边学习操练骑术,射术。 如果有可能,将来会参加那达慕大会,成为蒙古进士,亦或者等到某位藩王就藩,来草原招募亲军时,去向应召。 近些年来,草原上的人口增多,不少人都爱去种田,有的去北海那里混口饭吃。 在草原上,虽然牛羊不准越界,但对于自由来往的牧民,可没有什么界限,只要不啃食人家的牧草即可。 这时候,门外传来了几声欢快的犬吠。 然后一个圆脸的中年蒙古大汉,披着从汉人那里买来的斗笠,湿漉漉地掀开了帐子。 “阿布!”朝鲁喊了一句,虽然依旧在煮着热粥,削着几块肉碎入锅中,不时地捏着碎盐,心思不宁。 “快入冬了,雨越下越多了!” 男人脱下斗笠,大饼脸上露出一丝微笑:“我离开这几天,苜宿草长得咋样?” “长得极好,咱们的窖中能藏满呢,整个冬天都不用愁了!” 听到这,朝鲁才回过神来,笑着说道:“冬天还能多下几个崽,吃着羊奶呢!” “羊不要紧,得多养牛!”男人忙道:“我打听了,现在一头牛可能卖十块钱,抵得上二十头羊,值钱多了!” 朝鲁闻言,点头称是。 “这苜宿草是真的好,以往这几千来亩地,养一百头羊就撑死了,如今来看,再养一倍也成。” 男人高兴道:“明年我们再养十头牛,卖了给你娶媳妇!” 苜宿草别看适合草原生长,但是从来就没有大规模的普及过,一直都是中原在种。 因为对于牧民来说,地广人稀,遍地都是青草,根本就没有必要浪费人力来种苜宿草。 但随着大明对草原的征服,一个个千户区,百户区的限定,使得牧民们走场的地方被迫定居。 大多牧民只有冬歇草场和秋放草场,空间被压缩。 让他们定居的因素有三个。 青贮,让牧草发酵,足以保持牛羊过冬,使得越冬牧场不再那么紧缺。 苜宿草,让劣质的牧场草量大增,能养活更多的牛羊。 喇嘛庙,让信仰成为牧民的锚点,不得不以其为中心。 当然了,定居的舒适度也比游牧来的强,物资交换什么的也方便,也越来越受到牧民们的喜欢。 闻听这话,朝鲁大喜:“阿布,您说定了?” “朱勒豁得,朱家是你额吉的娘家,他们好说话,几个女子也踏实能干,只要三头牛,十头羊就能嫁过来!” 男人叹道:“现在娶女子越来越贵了,前两年两头牛就够了,哪里需要什么羊啊!” “所以我得提前给你定好了,不然还得涨!” “明年秋天娶亲,后年我们赖哈图德家就能添丁了!” “阿布,是赖家!” 朝奉还未言语,只听到一声插话。 旋即,一个年轻的身影走了进来,脸上泛出喜悦:“大哥,恭喜了!” “什么赖家,我只知道赖哈图德家族!” 大汉摇摇头,然后舀起一碗汤来尝尝,似乎嫌弃太淡了,又加了点盐。 “呼德,我的兄弟,你回来了!”朝鲁高兴地拥抱起来,对于幼弟的归来很是高兴。 “是啊,我怕你们收割苜宿草累了,所以就回来帮忙,二哥在喇嘛庙里也托我带了一些香油,这是供奉在菩萨面前。” 呼德笑道:“加在饭菜,能够保佑我们家长寿安康!” “阿弥陀佛!”这时,阿布则恭敬异常,双手握十,将香油缓缓地提过来,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 “这是我们家最贵重的东西,只有等到客人来的时候才吃!” 呼德则道:“阿布,以后在家里说说就罢了,在外面要说咱们家是姓赖!” “知道了——”拖着长长的尾音,老头颇有几分倔强。 呼德只能无奈。 所谓的姓氏,在蒙古与西臧一样,一开始是并不存在的,只有贵族们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。 如显赫得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。 就算是普通人,也只是把父辈的名字与自己的名字加起来,就组成了一个姓名。 但对于朝廷来说,这是毫无规律,且不方便的。 故而,蒙古地区早就进行大规模的赐姓,亦或者说进行汉译。 如,孛儿只斤氏,就译为鲍、包、宝、博、奇、罗、波;乞颜氏则为齐、祁、陈、秦。 兀良良则是乌、吴、于、魏。 越是大姓,汉译的姓氏也就越多,从而分化蒙古贵族和部众。 孛儿只斤氏更是不得擅自取用,只有朝廷批准的贵族,才能取之。 普通的蒙古人,自然是选择朝廷为他们挑选的蒙古姓氏,以及对应的汉姓。 之所以不只是汉姓,完全是因为普通的牧民根本就不懂汉字,告诉他也记不住。 蒙古姓氏则不同,口语话,易记。 当然,在户牌上,自然是只有汉姓。 这对于蒙古人来说,不亚于一场社会变更。 底层的牧民拥有自己的姓氏,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独立个体,不再是依附贵族。 拥有姓氏,看起来不甚起眼,但却是瓦解蒙古部落制,撅起根基之法。 几百帐牧民,所有人都拥有姓氏,而且还是不相同的姓氏,凝聚力将会大低,贵族煽动其造反的可能姓也会大降。 这是阳谋,也是大势所趋。 呼德在千户所的私塾虽然只是旁听,但多年的耳熟目染,儒家思想影响颇深。 在他看来,所谓的蒙古姓氏,不过是画蛇添足,家里沿用真正的汉姓,才是最好。 蛮夷的姓,何等卑贱…… 到了晚上,一家人聚在吊锅前,吃着热乎乎的肉,尝着里面的几块碎肉。 饭后,更是一人一杯暖洋洋的奶茶,让所有人都放松下来。 唯独呼德不爱奶茶,吃着淡雅的清茶,让父母,尤其是阿布哼哧了几句: “瞧你那模样,要不是穿了袍子,还以为你是汉人呢!” “阿布,这清茶最好喝,你们那是瞎耽误工夫,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滋味!”呼德满脸遗憾道。 男人懒得理这个逆子。 翌日,一家人齐上阵,拿起弯刀割上了苜宿草。 十几亩地的苜宿草,足够让他们一家四口干上十几天了。 阿布锤了捶腰,看着天空中淡薄的太阳,又看着手中锋利的镰刀: “当年我要是有这东西,我们部落早就起来了,搞不好我就真的成了贵族头人!” “如今就跟汉人一样,还得下地干农活,实在是可惜!” “阿布,别做梦了!”呼德毫不给面子:“这快活日子以往可没有,那些贵族老爷在的时候,您能喝奶茶?奶酒都喝不到!” “混账!” 父子二人斗着嘴,干起活来却非常麻利。 就在日上中天的时候,忽然一只零散的队伍跑了过来。 他们骑着马,头上戴着草帽,腰间挎着弯刀,一个个衣衫颇有几分破旧。 父子三人立马警惕起来,猎犬也吠起。 为首一人则提前下了马,身上并没有武器,显露出自己的真诚: “我们是草客!” “什么是草客?”朝鲁一愣。 “就是专门帮你们收割苜宿草的。”男人喊道: “你们这十几亩的苜宿草,收集起来起码得半个月,而我们这些人帮你干活,两三天就能结束!” 见到父兄二人懵懂,呼德这才解释道: “最近几年种苜宿草的人多了,就有许多闲散的人凑在一起,专门帮人家收割牧草,然后赚零钱!” “越是靠近汉人的地方,就越多。” “也有生歹意的,然后就被清剿了!” “多少报酬?”这时候,老阿布眉头一皱。 “一人一毫钱!” “太贵了!” 二人讲了一阵价最后以提供吃喝,并且每人十斤羊毛的价格达成了协议。 相较于钱,牧民们的羊毛更多,所以他们更热衷于以物换物,而非直接的出钱。 这样一来,得到了七八个生力军,到了第二天下午,所有的牧草就已经收割完毕。 而这群草客们也背着羊毛,兴冲冲地离去。 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在家里吃闲饭的人,或者说是准备参加那达慕大会,藩王招募,在闲暇时间赚钱,减轻家庭压力。 但呼德问时,还有两三个人直接道: “想要攒钱去喇嘛庙出家!” 呼德一惊:“喇嘛庙出家,可是没有女人啊!” “喇嘛庙不用干重活,还能为家里祈福,偶尔出去给贵族老爷们做事,也能赚钱……” 呼德沉默了。 在草原上,实行的是格鲁派,拥有着严格的教规,不得亲近女色。 但在某些人看来,这不过是一点小遗憾罢了,提前成婚,留下子嗣即可。 到时候出家成为了喇嘛,不仅地位高了,而且还会赚更多的钱养家糊口,比起当兵,或者搏一搏那达慕大会,强太多。 如果表现出色,还会成为庙里的僧官,地位崇高。 对于那些无法继承家产的次子们,实在是具有莫大的吸引力。 朝鲁锤了锤腰,他看着有些失神的弟弟:“怎么了?” “大哥,这群人疯了!”呼德摇头道:“不想着尽忠报国,只想着出家走捷近。” “入世为官,才是最好的选择啊!” 在儒家的价值观中,出家是躲避现实,且不孝的举措。 人丁的消减,对家族来说也是不利的。 “那是你们的想法了!”朝鲁摇头憨笑道: “我只想着继承家业,娶妻生子!” 呼德陷入沉思: “越来越多的人想当喇嘛,这草原变得让人不认识了……”
- 首页
- 最近阅读
- 快速导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