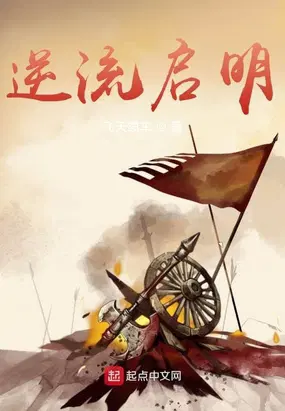绍武朝的官吏数量,相较于前明,爆涨了近两倍。 其中许多胥吏被纳入名录,接受俸禄,受到吏部的管辖。 而省试的举行,又让许多的秀才、举人参与衙门中,一下子就断绝了胥吏的世袭。 同时,胥吏由省试提拔,虽然造就了一些不懂得基层工作的读书人,但却提高了其素质,更加有助于地方主官对地方的控制。 且胥吏是本土任职,而省试后的吏员,则是本府随机分配,异县为官,能够很好的杜绝其结党营私。 故而,民间言论:吏员如官,吏治甚于前朝多矣! 这也为绍武朝的新政实施,奠定了基础。 减租减息,三乡老,通判推官,赋税直收,推广农作物…… 这一桩桩,一件件,才造就了如今这盛世。 据吏部统计,平均每县官吏数目,从前明时期的百来人,扩充至两百余人,近三百之数。 其中,既有巡检、仵作、僧道阴阳官等,又有六房书办,吏员,以及民间的乡老。 府、省的官衙,也逐步扩充数量,才能管辖如此庞大的官僚。 由此,中央的文武官吏,约莫五千来人,而地方则超过了四十万。 而实质上,官衙还大量雇佣了白役干活,其数量是官吏总数的三到五倍。 笼统的来说,大明朝两亿人,吃皇粮的人数约莫有在三百万,其中包括了军队、百官、吏员、白役等。 官民比例,约莫七十比一。 而要知道,前明时期吃皇粮的不过二十万,就备受文人们苛责,财政负担太重,皇帝不断的进行苛扣,经常拿纸钞、胡椒等抵债。 这些人的俸禄,一年总数超过了六千万。 其中,军队包括京营、边军、巡防营,总数约七十万,养他们就要三千万。 想到这,一向与钱粮相伴的阎崇信,忍不住哆嗦道: “我朝官吏之数,远胜于前朝,古往今来数千年,也唯有我朝官吏最多吧!” “年支六千万,古之未有啊!” 礼部尚书赵郎星闻言,也叹道:“中堂所言极是。” “近些年来,民间许多士绅言语裁撤官吏,开源节流,朝廷官吏太多,让人难安啊!” “不过说起来,如此多的官吏,在中堂手中依旧能够稳妥安置,俸禄不曾拖欠,实乃少有啊!” 阎崇信闻言,略显得意道:“官吏繁多,某在内阁也是经常难安,思索再三之后才略有所得。” “这大明,全靠商税维持。” 去年的秋税渐渐抵达京城,数量与内阁估计的相差不离。 比较现象级的是,绍武十八的商税第一次超过了农税,这对于内阁来说,是极具震撼的。 地方上缴九千万块银圆,而粮税只只有四千万左右,如果换算成粮食,一石八银毫,那就是五千万石。 相较于前明时期,几乎翻了倍。 内阁仔细研究,除了收税更为彻底之外,大部分的增长点在于台湾府、东北三地的开发,尤其是辽东地区,其地广人稀,京城所食之粮,泰半来自地。 而商税中,酒、茶、铁、盐四项为杂税,仅仅靠盐,一年就上缴两千万块,着实离谱。 其余与地方分成的关税、坐税,也上缴两千万来万。 再加上一些零零散散的,达到了五千三百万块银圆。 所以在阎崇信眼里,绥远和察哈尔商税收的多,而安南除了粮食一无所有,在安南和绥远之中选一下,他宁愿选绥远。 阎崇信对几人讲解着赋税的要点,感慨不已。 如果去除商税,那么仅仅看四千万的粮税,根本就养不活如此庞大的军队和官僚。 这般,就导致了官僚体系依赖于商税。 “重农抑商,断不可以行了。”户部侍郎苏子翁附和着,然后愤慨道: “许多不知深浅的,言语朝廷轻农重商,与民争利,这要是不争,朝廷怎么能活得了?” “难道要像前明时期的崇祯皇帝那样,向百官来化缘养军吗?” “好了!”阎崇信安抚道:“都是一些少不更事的,朝廷把税收到他们头上,自然就心绪难当。” “莫要听其胡言乱语。” 而一旁的赵郎星无言以对。 他算是看明白了,这两位是过来唱双簧,表演给自己看的。 前几日,他家的应为漏缴关税,被罚了两千块银圆,这些时日对于户部一直摆脸子,看不顺眼。 阎崇信瞥了一眼赵郎星,见其抿着嘴唇不发一言,他心中一笑,对着苏子翁微微点头。 苏子翁也配合道:“要我来说,朝廷每年剩下一千来万,为了以防万一,商税还是要收多一些。” “中堂,不如效仿前宋,施行官营如何?” “官酒,官盐,官醋,官茶、官布,照我来说,这样一来商税起码能再翁三五千万,这要是突破了一万万两,才算是真正的盛世啊!” “不行。”赵郎星再也坐不住了:“赵宋冗官、冗兵,还要上供给蛮夷,自然苛扣百姓,如今我皇明亲政爱民,断不可行此事。” “怕是一旦施行,民间就不稳了。” 他家就经营着大量的醋场,酒场,这要是收归国有,朝廷亲自经营垄断,那还赚个屁呀。 “安坐!”阎崇信微微一笑,不紧不慢地问道: “为何商税倍于前朝,而百姓们却不反?” “下官不知。”赵郎星平静下来。 “我也曾疑惑,陛下亲解道,此为直接税和间接税。” 阎崇信摇摇头,站起身对着紫禁城的方向拱了拱手,表达了对于皇帝的敬仰: “所谓直接税,谓之农税,亲自从农家手中取走,自然是人皆恨之。” “而间接税则不然,如布匹,价格高了些,那衣服就在多穿几日,等实在穿不了,就跺了跺脚再买,那时候只会骂奸商,何怪朝廷?” “况且,能买得起或许的,口袋之中总是存了些许钱财,买不起的自然就不买。” “所以,商税不仅得征收,而且还得不断收,一直收,农税则相反,尽可能的轻徭薄赋,百姓们口袋里有钱,商税才能收起来。” 赵郎星恍然。 他沉默了一会儿,开口道:“下官明白了。” 阎崇信微微颔首,露出了真切的笑容。 事后,其才快步而至京城,向皇帝汇报此事。 朱谊汐听其解释后,才叹道:“到底是读过书的,知晓分寸,讲明白了就好。” “些许的读书人,为官多年,忘记了圣贤书上的道理,一心被银钱遮住眼睛,着实该磋磨一番。” 阎崇信拍着马屁:“陛下怜悯,让其改过自新,实乃是千古圣君也。” 对此,朱谊汐摇摇头人,继续裁剪着眼前的一颗花树。 手中的剪刀飞快,不一会儿就将整颗树修剪得坑坑洼洼,就像狗啃了一般,分外的难看。 阎崇信见之,眼皮抖了抖,就当没看见。 朱谊汐则不然,反而认真的打量起来,看样子满意至极。 见其脸色不变,他才道:“修剪树木,看的不是当今,而是往后。” “减去那些枝叶,留下空间给新枝,从而让其更加美观动人,一时的美丑算不了什么,最重要的是未来。” 阎崇信闻言,神色一禀,似乎有所悟。 实际上,朱谊汐的心情并不太平静,他只是借着修剪花树来使自己平静下来。 如果是在当年,官员如果喊几句与民争利,他早就耳光子扇过去,直接一贬到底,来个排气泻恼。 但如今登基日久,他成熟了,知晓了稳重。 赵郎星,礼部尚书,表面上看是一个人,实际上他的身后站着一大串文武官吏,处置了他根本就不见效。 这群人,可以将其代称为既得利益群体。 他们又与明末时期的士绅不同,这群人是由官商群体构成。 家族中推出人来当官,然后族人经商,相互勾连,支持,从而势力庞大。 毕竟科举这玩意儿,除了要脑子外,钱财占据很大的份量。 最典型的代表,就是山西晋商群体。 人家徽商是穷山恶水,不得不出来经商,而晋商则得益于边贸,主要的人才放在经商上。 这种人让朱谊汐想起来了英国的新贵族群体。 何谓新贵族,就是不再依靠土地,而是靠经商发家致富的贵族,思维上更加广阔。 按照常理来说,苏格兰发生叛乱,查理二世想要加税解决军费问题,这是很正常的思维。 但新贵族不肯,要求限制征税权,不同意立马就造反了。 所谓的天主教信仰问题只是借口,主要是利益。 这行为大明则是什么? 江南不纳税的士绅。 盐税一年百万,茶税几十万,根本就在糊弄鬼。 而如今,农税减轻,绍武朝中央集权力度加大,士绅们不得不屈服,大多缴纳田税。 而这时候,重税的商人群体不乐意了。 尤其是有钱有势的官商,本来能赚百分百的利润,如今要掏三成给朝廷,着谁忍得了?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,朝廷从上至下的重商思维,让商人的地位曲线性升高,其诉求自然就出来了: “减税!!!” 在思想上,他们以经世治国为口号,大肆要求朝廷重视商业发展,减轻商人的负担。 而在行为上,他们则要求朝廷重视商人利益,如减轻赋税,减少关卡…… 表面上来看,这是很正常的诉求。 但这与朝廷的利益冲突了。 因为从幕府时代开始,就对商税大肆征收。 如川盐入楚,楚粮入吴,依靠着长江这条黄金商道,幕府不断地征收商税,养活了十万大军。 不然的话仅仅依靠被肆虐的湖北地区,简直就是难如登天。 为了安抚商人,朱谊汐就不断地出台政策,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,肃清吏治。 如南京登基时,他废除贱户、杂户,一律统称为民户。 表面上来看是贱户得利,实际上却是大量的商人们获得了实质上的好处。 因为在前明时期,除了江南地区少量商人外,大量的商户是很难考取科举的。 皇帝出台的政策,为其子嗣登科举扫清了障碍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不再如是。 中央朝廷的每项政策,都有深意。 同时,贱户变民户,就代表着其不再享有免税的政策,一切行事都要征税了。 换句话说,从现在开始,青楼也要缴税了。 官员们讨厌贱户,除了其身份低贱外,还有一项原因就是因为其不纳税,不服徭役,无利可图。 雍正时期的废除贱户,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扩大税源,进行收税。 沿海漂泊的疍户、江南地区的惰民、丐户等,也纳入人口户籍,缴纳赋税。 不然的话人家满清皇帝,八旗贵族们都照顾不过来,哪里想得起几百上千年来的贱户? 历朝历代不管不顾,也是说明其无利可图。 税收这种事,农税轻了,商税就会重,非此则彼,根本就没得平衡。 而如今,绍武皇帝选择轻田税重商税,这就让一群过惯轻松日子,且实力逐渐膨胀的商人们不舒服了。 官员要求重商,其背后都是一群商人在支持,或者本身就是经商。 面对这些人,不管不顾地处置,不过是强行压制矛盾,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罢了,不值当。 “前明依赖于田税,故而对士绅再三小心,我朝依赖于商税,对这群商人们也得注意了。” 正是因为想的这般深,朱谊汐才有气。 今日减税,明日就争权,后日就是推倒皇帝。 这在西方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。 而东方由于长时间的君主专制,君主妥协就会死亡。 对朱谊汐来说,如果所谓的资本萌芽是要夺他的权,推翻他的家族统治,那这萌芽不要也罢。 权力就像毒药,只要一入口就摆脱不得。 “不过,有利也有弊。” 朱谊汐忽然又松了口气。 国朝赖以商税而活,就必然不会舍弃商税,不断地加码,维持财政的健康。 同时,自古以来,中国的农民就占据多数,这也就意味着读书人多出自地主群体,这群人或许重商,但绝对不会摆脱儒家思想。 毕竟儒家到现在的程朱理学,就是地主阶级改造后的产物。 “压制和发展,这并不矛盾。” 皇帝自言自语了一番,随后道:“你做得不错。” 阎崇信大喜:“这是臣应该做的。” “商税之重,国朝仰之,岂可轻动?” 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