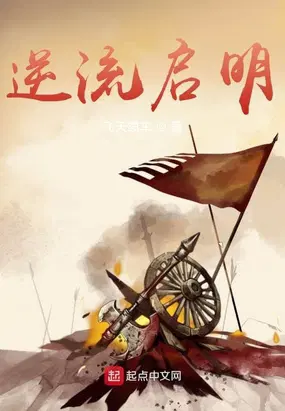秦学大昌,在北京以顾炎武传学,弟子上千,屋舍数百,捐赠的学田就超过千亩。 顺天府甚至愿意给顾炎武办学校,但被其所拒绝,表示不愿意效仿东林旧事。 说白了,就是不想再造就党争,从而断送这门学问的前途。 而在地方上,郑森在吕宋府、黄宗羲在赵国、王夫之在北海,朱之瑜在浙江余姚,方以智在浙江、李题在陕西、直隶容城孙奇逢等,各自宣扬秦学。 但归根结底,其主体思想就是经世致用,反对务虚空谈,提倡农商并举,广征商税,民重君轻,可以说是与东林党反着来。 但每个人在思想细则又有不同,郑森要求重视海贸,减少关税;方以智要求重视几何,西学中用;黄宗羲强调读史,民本为先;孙奇逢则要求慎独,将格物致知和致良知结合。 虽然分为各个派系,但秦学的发展壮大却是无需多言的。 可以说,广大的士林皆认为,秦学取代理学,就如同理学取代玄学,顺理成章。 因为就像是顾炎武所说,秦学本就去从理学中诞生的,大部分的思想不过是升华提炼了,还加了部分心学的内容。 最关键的一步,就是官方的认可,即科举认同。 这一步极其艰难,甚至顾炎武觉得,自己这一生怕是看不到了。 朱之瑜刚落座不久,忽然有一人脚步迟缓而来。 “咳咳!楚屿,你怎么来了?” 朱之瑜抬眼一瞧,立马惊起,双手拜下:“夏峰先生,您怎么来了?” “哈哈哈,我本就是直隶人,来一趟北京算的什么?” 孙奇逢哈哈大笑,然后毫无拘束地一屁股坐下。 孙奇逢本是进士出身,因为反对阉党,故而在乡间教学,结庐而居。 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明亡后,由于故园被清军圈占,孙奇逢举家南迁至河南辉县。 夏峰村位于辉县苏门山下,紧靠名泉百泉,山清水秀,地僻清幽,故而孙奇逢从此隐居夏峰。 此间清廷多次征诏,甚至以国子监祭酒之职相聘,均遭拒绝,时人尊称其为“征君”。 其以陆象山、王阳明为根本,以慎独为宗旨,以体察认识天理为要务,以日常所用伦常为实际。 故而,他修身苛刻严厉。 在思想上,他将“道问学”与“尊德性”合二为一,最后,总结出了“躬行实践”、“经世载物”的思想。 他认为做学问的,不应是空谈家,应注重实践,重视经世致用。 这般,在北方孙奇逢与顾炎武并称为“孙顾”,又称之为北方二峰,难以越过。 即使与顾炎武并称为北顾南朱的朱之瑜,也不敢放肆。 “今日访友,倒是碰到了朱小友,甚好。” 孙奇逢胡子花白,但精神矍铄,看样子还能再活十来年。 朱之瑜苦笑道:“若知孙老在这,在下岂敢放肆?” 几人相视而笑,一切都在不言中。 秦学大昌,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。 立功,立言,立德。 立功不好说,几人感觉没什么大功,德行是仁者见仁,但立言却是可以的。 一旦秦学成为官学,那么几人就是勤学的立派宗师,其言行书籍就会成为官学的一部分。 这样一来,像朱子一样流传千古就指日可待了。 这是儒家毕生的追求,谁也逃脱不得。 谈到了秦学,孙奇逢倒是有话讲了,他捋了捋长须道: “如今士林皆以东林为恶,故而多行反思之举,由此带动了一门学科。” “训诂学。” “训诂?”顾炎武与朱之瑜一愣。 所谓“训诂”,也叫“训故”、“故训”、“古训”、“解故”、“解诂”,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“训”;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“诂”。 平白的解释就是,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、语法、修辞等。 其特点就是捧古贬今。 无论是文章诗词,都是越古越好。 “训诂学之兴起,莫过于咱们秦学大昌,有些人不悦,故而以两汉、盛唐为宗旨,企图驳斥我之学。” 孙奇逢摇头道:“似乎效仿了两汉之学,我大明就将大兴,故而斗倒咱们的秦学。” “党同伐异罢了。”顾炎武毫无畏惧道:“当年心学兴起,那些大儒们从朝廷到地方,无不驳斥,抵制,但心学却不断兴盛,直到如今。” “当年的张江陵,不也是心学传人。思想这东西,是阻断不得的。” 朱之瑜更是毫不避讳道:“孙老,刚才我们二人言语,秦学之盛,在于上,而不在下。” “朝廷和皇帝支持,底下的大儒们再怎么固执,也无济于事。” 孙奇逢恍然。 吕宋,镇海城。 郑森屹立在城头,迎着海风,举目而望。 不远处的港口,白帆林立,船只大量的停泊在码头,卸下了大量的货物,同时也带走了吕宋的特产。 为这港口繁忙工作的力夫,达到了万人。 不过在港口,一座三楼建筑极其显眼,海关衙门四个大字抬头可见,似乎是石牌,镇压着码头一切。 路过的行人一个个面带畏惧,快步而行。 郑森心里清楚,这条港口虽然流淌着黄金和白银,但吕宋只能吃点残渣,大头都被海关衙门给吞吃了。 吕宋的香料,甘蔗,棉花,金鸡纳霜,贵木,矿产,几乎在为海关做嫁衣。 但没办法,海关衙门是皇帝私衙,是内帑金钱由来,他要是断了海关的收入,那么明天皇帝就会断了他的前途。 吐了口浊气,郑森陷入了思考:“来到吕宋两年,除了知晓一些西夷的风俗外,就只有改土归流了。” “再待下去,怕是没什么效果,也该是时候回到京城了,五年我可等不来。” 吕宋总督五年一任,吹着海风,享受着高额的福利,但这都不是他想要的,没有功绩,对他来说就毫无吸引力。 “必须回京,哪怕是只是小九卿,也比在吕宋浪费时间来得强。” “总督!”这时,一个黑发的西夷人穿着薄纱制成的官袍,恭敬道:“学院将开学了。” “嗯!”郑森对其相貌熟视无睹。 在吕宋,西夷人占据了近一成的总额,土地众多,纳税也是积极,而且还积极的参加科举。 无论是语言还是习俗,亦或者衣物,其都不断趋向与大明。 对于他们,郑森就以归化蛮人待之,不偏不倚,倒是习惯了。 如今在吕宋总督府,西夷人占据官吏总数达到了三成,配合着总督府的统治。 坐上马车,郑森闭目养神。 由于吕宋湿热,故而无论是衣服还是吃喝,都进行了改良,而马车自然也不例外。 狭窄且闷热的马车,变成了透风而又凉快,坐在其上,阳光晒不到,但却透着风,可以说是舒适了。 不一会儿,马车来到了城北。 一处占地约二十亩地学院就出现在眼前。 郑森这时候兴致才起来。 对于秦学,他自然是认同的,同时为了撇清东林学派的关系,一直大力支持秦学。 因为他知道,皇帝支持秦学就够了。 一众的读书众,秀才不过三五人,都不过二十来岁,精神奕奕,他们都在仕途上前途不小,故而不在官场,没有参加省试。 其余的部分,都是一些童生,以及一些儒童。 所有人加在一起,也不过两百来号。 总督一来,所有人立马躬身迎接。 郑森习惯了,言语了几句,就亲自书写了牌匾: 吕宋学院。 一时间,气氛热烈。 这虽然不是官学,但却是商人们合理支持修建的,传授的不仅是秦学,还包括了几何等科举内容,实乃进阶的的好去处。 大量的西人父母也在此,对于吕宋有一个好学府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。 举业要想大成,没有学府,闭门造车可不行。 这时候,商人们反而是最憧憬的,因为他们迫切的想改变家族的门第,从商人变为士族。 郑森注视着如此场景,忍不住感叹道:“秦学大昌于吕宋,自我郑森始。” …… 浙江,余姚县。 城东,谢府。 相传谢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陈郡谢氏,世代高门,不受朝堂更替的影响。 但到了隋唐,关陇门阀兴起,垄断了朝廷上高官公卿,故而关东的世家们纷纷衰落,江南尤甚。 不过随着安史之乱,关陇门阀势衰,不得不让权于河北世家,崔、王等河北大姓崛起。 江南的世家们愈发没落,跌入尘埃。 谢氏落到如今,已经不是百年的时间了,而是几百年。 谢安国不知晓祖辈的光耀时刻,但却明白,自己的已然到了重要时分。 书房中,一道日本细绣屏风后面,便陈列着精装书籍的大书架,藏书约有千册。 在旁边,红木椅子、椅子上铺着绸面的羊毛垫,波斯地毯他用不起。 在谢安国的桌案上,则放着大小一整排名贵毛笔,湖笔,狼毫笔都在此,就算是镇纸,也是温润的碧玉制作,极其昂贵。 雕窗上以碧纱为面,园子里的景色若隐若现,仿佛一副绿色水彩的风景画。 “哗……哗……”寒风风吹拂着窗外的树叶,凋落着最后几片艰难留存。 其好像某种独特的音律,比丝竹管弦单调,却更加磅礴自然。 谢安国却听着窗外的风声,手中握着笔,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。 他留着短须,不长不短,是在两个月前留的,显得他有些成熟。 就算是身上的衣物,也是去除了华丽,灰白色在身,布靴在脚,甚至为了体现斯文,桌案旁边还放了一个眼镜。 毕竟在读书人的圈子中,阅书百卷必然是近视眼,需要戴上特制的眼镜才可舒服。 不知何时起,戴眼镜就意味着读书多,不戴就意味着偷懒。 谢安国特意制造了一个无碍眼镜,除了装饰作用外,其他影响一点都没有。 这时一个穿着布袍梳着发髻的中年人走到屏风旁边,忙喜道:“少爷,县里的赵主薄登门拜访。” 谢安国一听眉头便是一舒,想了好一会儿,用一种夹杂着喜悦和激动,以及强行按耐住的口气道:“开大门,快去迎。” 他立马停止发呆,起身拿起方巾,仔细整理了一下衣装,想了想,他戴上眼镜,这才三步并两步地走出书房。 到了大厅口,他立马平稳了心情,放慢脚步,忙作揖道:“本该出府门恭迎赵公,但又因衣冠不整得换衣服,怕您在外面等得急了。” “哈哈,谢公子莫要拘泥那些繁文缛节,你我世代相交,可谓亲近。” 宽脸皂鞋,穿着黑色长袍的赵主薄,脸上再也没有了官威,把如同和善的隔壁叔伯,眉开眼笑。 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,平日里根本就见不着面,哪来的相交? 谢安国心中愈发肯定起来。 “你那县学的教谕,与我是好友,平日里一起下棋玩耍,莫要太过见外,你就叫我世伯吧!” 赵主薄亲近道,旋即环顾四周,啧啧道:“不愧是陈郡谢氏,多年来的士族大家,几百年过去了,屋子里掉下了一根钉,其沾染的书香,都比我家的浓厚些。” “您谬赞了。”这时候,谢安国倒是端起来了:“世伯,不知可是省试有了消息?” “没错!”赵主薄高兴着,如同自己中了一般:“省试出来了,贤侄高中第八名。” 说着,他低声道:“按照规矩,省试前十名了授通判一职,如今你我算是同僚了。” 谢安国大喜过望。 按照省试的规矩,前三名授知县,三至十名为通判,前二十名则是主薄、县丞,余下的则是各房书吏。 如今在县衙中,主薄不过正八品,而通判则是从七品,官阶还在其上。 可以说,此时此刻,谢安国已经是其上官了。 由不得其不客气。 “当不得如此。”谢安国谦虚道:“省试还未下,一切还犹未可知,老父母莫要多礼。” 赵主薄尴尬地笑了笑:“是了,但贤侄前途无量,莫要忘了我这个世伯才是。” 谢安国心里直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