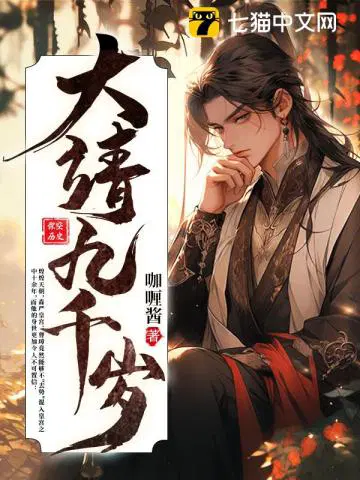不知近水花先发,疑是经冬雪未销。 纷纷扬扬的大雪从上空飘下来,先是柔软的鹅毛飘飞,将森严的皇宫变成了金银明亮的白宫,初冬的大雪飘下来,已是太康三十八年的年尾了。 初晨。 天蒙蒙放亮,到处挂着的灯笼仍然点着,天地白茫茫的一片,各宫当差的太监宫女拿着扫帚清扫着道路上的雪。 太康最是喜欢雪的,得知昨夜飘了雪,便早早地起来,往畅春园踏雪赏景。 早上的雪依旧没有停,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 太康穿着貂毛领口棉袍,带着暖耳冬帽,面容喜悦地踩着雪发出‘擦擦擦’的声音,天地白茫茫的一片,眼前的墙、树、屋檐都被大雪覆盖。 下雪是不冷的,太康哈着热气搓着手,信步走着,边走边赏雪。 后面跟着冯珙、陈渊和四个御前侍卫。 “主子爷!这是初冬的瑞雪,”陈渊跟在旁边陪着笑,“用民间的话说,这叫‘瑞雪兆丰年’,说明来年肯定有个大丰收。” 冯珙知道陈渊是最会阿谀的,低着头面无表情的跟着。 太康脸上挂着笑:“嗯,这叫…冬天满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哈哈哈!明年呐准是个丰收的好年。” 陈渊陪着笑:“明年大丰收,只要官吏们上下齐心,准能装满各地粮户的粮仓!” 太康闪了一眼陈渊,问:“怎么,难道还有不齐心的?是不是又有不好的奏折递进来?” “圣明无过主子!是扬州两淮的官员递上来弹劾两淮盐道御史的奏折,”陈渊小心翼翼地说,“今儿早上才送到的,奴才怕扰了主子赏雪的兴致不敢提早说,但也不敢不说。” 太康脸色一沉:“奏折在哪里?” 陈渊从怀里拿出奏折,双手奉上。 太康看了眼棕色封皮的奏折,又看了看哈着腰低着头陈渊,拿起奏折,打开看去,是两淮官员弹劾两淮盐御史金涛的,里面还有盐道督监的影子。 这个盐道督监是宫里面派出去的人。 大靖朝历来就有派遣太监出去督军、督盐、督铁、督粮的,这些人都是皇帝信任的人派出去的,大多数都是冯珙、陈渊、石安和郑经这几个秉笔太监的心腹之人。 两淮盐道督监就是石安的心腹——周福宁。 看完奏折,太康将奏折合起来拿在手里,双手背在后面,低着头朝前缓步走去,却已经无心赏雪了,脚下依旧发出‘擦擦擦’的声音,让他有种烦躁的感觉。 冯珙和陈渊静静地跟着。 “冯珙!”太康突然停住脚步,抬起头望着前面的茫茫大雪问,“朕记得没错的话,这个金涛是董阁老举荐的吧?” 冯珙上前一步哈着腰:“回主子的话,金涛是太康二十三的进士及第,是董阁老的门生,原任翰林院学士,后升任户部侍郎,是太康三十五年董阁老举荐为两淮盐道御史。” “此事董阁老知道吗?”这话是在问陈渊。 陈渊赶忙道:“这是密折直接送到司礼监的,今儿早才送到,董阁老目前还不知道。” 太康仰面叹口气,“今儿是十二月了,皇后娘娘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了。”说话间,他将奏折踹进怀里,“给两淮官员传旨,此事务必谨慎详查,陈渊!派北镇抚司十三太保前往两淮调查此事,还有!宫里派去的盐道督监是干什么吃的?恐怕也贪了不少吧?给朕押回来!” 原以为太康会龙颜大怒,没想到他会谨慎处理。 不过也好,虽没能处理掉董阁老,却意外的把石安给牵扯进去了,早就想除掉石安苦于一直没有机会,这个机会,千载难逢。 石安一倒,曹璋就是去了保障。 单靠他想在司礼监活下去,怕是还太嫩了些。 郑经已经是风烛残年,对他构不成威胁了,石安一走,整个司礼监就剩下冯珙这么一个对手了。 陈渊暗暗盘算,急忙回应着:“奴才遵旨。” 得到旨意,陈渊赶紧退去准备。 太康朝着前方走去,冯珙紧紧地跟在后面伺候着。不多时,他们就走到了畅春园,整个院内被大雪覆盖,却没有丝毫的冷森之意,放眼望去,给人一种很大的视觉冲击。 天地一色,混沌一体。 太康背着手直直的往前走,走着走着他像是自言自语着说:“做人难,做官难,都不难。不做小人,做个好官,这才难啊!” 冯珙附和着说:“用民间的话说,穷汉有穷汉的苦,富汉有富汉的难,主子,奴才分不清好坏忠奸,只求主子能够龙体安康便是最好。” 太康哼得一笑:“你跟了朕二十余年了,到现在连个马屁都不会拍,手底下管着这么大的内宫,也不怕被人算计了。”这个算计指的是陈渊,“你看看人家陈渊,事事都往前头钻,即管着北镇抚司,又管着东厂,要不是你手里掌着印,恐怕早就被他给整治了。” 冯珙赔笑:“印是主子的,奴才只不过是替主子看着;北镇抚司和东厂是皇上的,是朝廷的,别人谁也拿不走。” “这话实在!”太康嘴角勾起一抹笑,很快又隐去了,“冯珙,你说密奏金涛贪墨之事是真是假?董路知不知晓?” 冯珙想了想说:“奴才不敢乱说,只好打个比方。” 太康饶有兴趣:“说。” 冯珙:“以奴才看来,董阁老像个媳妇儿。” 太康看向冯珙:“怎么说?” 冯珙:“上面有父母要伺候,中间有丈夫得体贴,下面还有儿女要照顾。” “像!”太康嘴角露出了笑容,“他这个媳妇儿难做,俗话说会做媳妇儿两头瞒,他是上不敢瞒君父,中不会瞒同僚,下不能瞒百姓。是不是他在贪,还是别人打着他的幌子在贪,此事儿等查清楚再说,还有,两淮的官员是如何知道金涛在